
樊增祥画像。资料图片
珍藏于山东省巨野县博物馆的《樊山判牍》。资料图片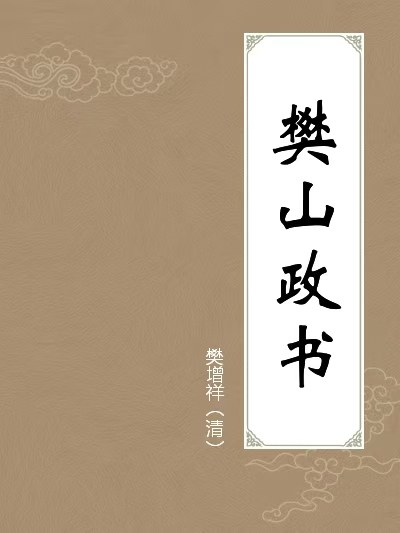
《樊山政书》。资料图片
樊增祥(1846年-1931年),字嘉父,号樊山,湖北恩施人,是清末民初活跃于政坛和文坛的知名人物,他不仅诗才敏捷,还以听讼治狱见长,时人称其判牍“以仲由折狱之长,杂以曼倩诙谐之笔,妙解人颐,争相传诵”(《樊山判牍序》)。《樊山政书》由樊增祥亲自作序,汇集了樊增祥自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至宣统二年(1910年)任职陕西按察使、布政使和江宁布政使期间的公牍,其中包含各类文书,以针对讼事所作的批词为主,为我们了解清代地方司法的运作实况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司法智慧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批,是清代的一种常用公文,主要为上级衙门对下级衙门以及衙门对属员的上呈公文(如详文等)的批示,审判过程中的批词可视为司法判牍的一种。在《樊山政书》所载的众多批词中,《批西安府张守详》一文堪称妙判,充分彰显了樊增祥的司法智慧。
该批词记载了这样一桩案件:高焦氏的丈夫早亡,她孤身抚养子女三人。亡夫的分居胞弟高有林生活贫苦,常得高焦氏的帮衬。案发前一年的二月,岁值奇荒,高有林向高焦氏借钱,高焦氏以财力不足而未予应允。三月二日,高有林再次上门借款,被高焦氏拒绝后大骂寡嫂无情,甚至将嫂子的锅碗瓢盆摔破。高焦氏一怒之下赶往高有林家理论。高有林之妻高张氏当时卧病在床,听到争吵声勉强起身上前劝阻,被正在气头上的高焦氏随手推开,摔倒在地而死。如此一来,亲戚间的琐屑纠纷竟酿成了一桩命案,以往多次接济夫弟的高焦氏竟成了杀人犯。
依照清代的司法程序,地方命案经州县初审后,州县需拟出初步的定罪量刑意见,再经府、按察司至督抚逐级审转复核,之后由督抚写奏章上奏皇帝。该案案发后,地方初步将高焦氏依据《大清律例》“斗殴及故杀人”条中“凡斗殴杀人者,不论手足、他物、金刃,并绞”之规定拟绞监候。之后案件上报至时任陕西按察使的樊增祥处,樊增祥在本案的批词中斟酌情罪、释法说理,为后人留下了一份优秀的古代司法判牍范例。该批词用语精练,篇幅虽短,却较为全面地覆盖了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和道德评价三方面的重要内容。并且,三者并非截然分开、各自独立,而是相互交织、融为一体。大体而言,批词开篇叙述案情,中间和结尾部分从法律和情理的角度批驳原拟罪名的不当之处并提出自己的审理意见,针对高焦氏和高有林的道德评价则贯穿全篇。相较于文辞和结构,该批词的释法说理方式及发挥的效果尤为引人瞩目,值得深入探究。具体而言,该批词在释法说理方面有两大值得今人关注的亮点:
其一,该批词在叙述案件事实和分析法律适用时,紧扣法律规定,兼顾客观案情和当事人的主观心理,并结合验尸报告等关键证据,有理有据、论证有力。批词开篇以简练的语言概述了高焦氏和高有林的矛盾以及高张氏被推开后倒地而亡的事实,接着从法律规定入手,明确“斗殴”的定义,表明“所谓斗殴者两人对殴,彼来此往,因而伤人致死者,乃得坐以绞候”,进而结合法律规范与案件事实,详述为何高焦氏的罪状与斗殴杀人不符。樊增祥指出,高焦氏因夫弟毁锅砸甕而上门理论,这种行为合乎常理,不仅称不上与其妯娌高张氏斗殴,也称不上与其小叔子高有林斗殴。高张氏扶病拢劝,并非参与对殴,而高焦氏对于高张氏的所作所为不过是随手推开,亦并非打人。批词还基于验尸报告这一确凿证据,指出高张氏的致命伤为“脑后磕伤二点”,进一步强调高张氏之死并非打伤所致。在讲明客观情形后,樊增祥还不忘“论焦氏之心”,即从主观层面展开分析,阐明高焦氏之所以赶赴高有林家,系“往寻其叔,非往寻其姒”,虽高张氏因此惨遭横祸,但病弱之人被随手一推后倒地震跌身亡,乃高焦氏意料不及之事,并非其有意为之的结果。故“肇衅由于尸夫,而死者由于病弱”“张氏之死,不死于其嫂”。在主客观兼备的分析之后,樊增祥顺理成章地提出了自己的审理意见,认定此案“宜以过失论”。此处之“过失”与今日刑法规定中的“过失”在主观恶性程度上有所不同,主要指“耳目所不及,思虑所不到”“无害人之意,而偶致杀伤”的情况。从对案情的描述来看,高焦氏的罪行的确更接近于清代的过失杀而非斗杀,樊增祥于判牍中经过论证纠正了原判在法律适用上的错漏。
其二,在理性的法律分析之外,樊增祥还从天理人情出发,对高焦氏抱以同情和理解,并不厌其烦地解释原拟审判意见的不合情理之处以及将由此引发的不良后果,增强了批词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对高焦氏因自顾不暇而推拒借款的做法,樊增祥称其“不得谓之悭吝”;对高焦氏在怒气驱使下前往高有林家理论的行为,樊增祥亦称“此亦人情”,不应过多苛责。从法律层面阐明了高焦氏宜以过失杀论处后,樊增祥还写道,哪怕在亲兄弟间,分居后互不帮扶的情况都很常见,高焦氏作为寡嫂却能多次出钱接济夫弟,实属难得。若其过去一味吝啬,则高有林不会在荒岁乞援。高焦氏“既做好人于前,反得奇祸于后”,怎不令人怜悯?再者,司法官员也应为遗孤考虑,母在狱中,两女一子,谁来照看?薄田破屋,谁为经营?若高有林起意鲸吞高焦氏财产,则为孽更大,后患无穷。以上字字句句,直抵人心。在犀利的笔锋下,流淌着怜恤弱小的脉脉温情和对世事人情的深入洞察,这种法理情相结合的论证方式,使批词更为打动人心,令人信服。
批词的最后,樊增祥郑重嘱咐下属“遵批更正,毋稍固执,切切”,使得案件的审转复核未流于形式,原判的错处得以修正。如此一来,这份批词发挥的积极效果不言而喻。依据清律,过失致人死亡者准斗杀罪论处,绞罪可依律收赎,将赎银十二两四钱二分给付受害者家属作为茔葬之资,带有一些现代人身损害赔偿制度的色彩。樊增祥以过失杀论高焦氏之罪,既免除了高焦氏的性命之忧和牢狱之苦,切实发挥了减少冤案、矜恤慎刑的作用;又给受害人一家以必要的经济赔偿,实现了情罪允协、不枉不纵,使案件双方当事人均得到了公平公正的对待。不仅如此,在注重个案公正的基础上,樊增祥还考虑到更为广泛的社会影响。试想,寡嫂高焦氏往昔多次接济夫弟,仅仅因荒年手头不便而拒绝借钱便被小叔子骂无情,进而牵扯进这一桩人命官司里,若再因随手一推所带来的始料不及的后果而坐以绞监候重罪,留下无人照料的子女,甚至被侵吞家产,不利于传统家族伦理和良好社会风气的维护。为此,樊增祥扭转了案件的走向,还于批词中频繁作出伦理道德上的评价,在开篇叙述案情时即穿插了对高焦氏的褒扬,称“焦氏推财帮顾,不得谓之不贤”,在结尾处也不忘重申“焦氏以一寡妇出余财以赒其叔,实为难得”。针对高有林因荒年借贷不遂便不顾昔日赒恤之情而摔破高焦氏锅碗瓢盆的举动,樊增祥则严厉指斥此乃“横逆无理”“异于禽兽者几希”的劣行。这样一份批词被收录进《樊山政书》中予以公开,能形成示范效应,为其他官员断案做出指引,进而发挥了扬善惩恶的社会功能,起到引导和教化民众的作用,收到一定的社会治理效果。
从以上分析可见,樊增祥的这份批词论证清晰有力,追求法理情相统一,充分体现了中华传统法律文化所蕴含的司法智慧。在国法方面,樊增祥援法断罪,结合关键证据,立足于案件的客观情节和高焦氏的主观意图,纠正了原判在定罪量刑上的偏差,保障了法律适用的准确性。在情理方面,樊增祥深切体察了高焦氏的可矜可悯之处,指出了依照绞监候处置的情罪不符问题,践行了保护鳏寡孤独、老幼妇残的恤刑原则,从而实现了司法审判中法理情的交融与平衡,维护了司法的公平正义。通过本案批词,樊增祥不仅还案件当事人以公道,还为其他官员听讼治狱提供了范本,具有导民向善、敦厚风俗的积极价值。
以上述批词为代表的古代优秀判牍对当下司法实践中如何在裁判文书里加强释法说理仍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法律并不是冷冰冰的条文,背后有情有义。要坚持以法为据、以理服人、以情感人,既要义正辞严讲清‘法理’,又要循循善诱讲明‘事理’,感同身受讲透‘情理’,让当事人胜败皆明、心服口服。”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为推动该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宝贵的智识资源和丰富的实践样本,将古代的司法智慧和传统经验融入现代司法审判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让司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的可行路径之一,有助于在司法裁判中实现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
判词原文:
批西安府张守详
查高焦氏系高有林分居胞嫂,其夫早故,遗有子女三人。有林穷苦无资,焦氏推财帮顾,不得谓之不贤。去年二月,岁值奇荒,有林复向其嫂称贷,焦氏以无力辞。当自顾不暇之时,亦不得谓之悭吝。乃三月初二日,有林复往告帮,不允则骂其无情,并将其嫂锅瓮摔破。如此横逆无理,其异于禽兽者几希。焦氏因其欺凌孤寡,赶往其家理论,此亦人情。有林之妻高张氏适当卧病,闻闹勉强下床,上前劝阻,焦氏时方气忿,随手推开,不期病弱之人,随推倒地,震跌而死,此焦氏意料所不及也。来详引“斗殴律”、“勿论手足、金刃、他物伤,并绞”律,拟绞监候,似未允协。所谓斗殴者,两人对殴,彼来此往,因而伤人致死者,乃得坐以绞候。今焦氏因小叔高有林忘从前屡次赒恤之情,挟荒年借贷不遂之恨,毁锅砸瓮,其势汹汹,其肇衅由于尸夫,而死者由于病弱,当焦氏入门理论之时,不但不与其姒斗,亦未与其叔斗也。妇人惜物索赔骂闹,是其常态。张氏扶病拢劝,非帮打也。焦氏随手推开,非打人也。尸格内填“脑后磕伤二点”,非打伤也。律以斗殴,情罪相乖。论焦氏之心,往寻其叔,非往寻其姒,而张氏之死,不死于其嫂,而死于其夫。以本司持平论断,只宜以过失论。分居以后,亲兄弟不相顾者多矣。焦氏以一寡嫂出余财以赒其叔,实为难得。向使一味悭吝,则有林知其手紧,亦不致荒岁乞援。是既做好人于前,反得奇祸于后,亦可悯矣。且诸君子独不为遗孤计乎?母在狱中,两女一子,何人照看?薄田破屋,谁为经营?设有林以肇衅之人,更肆其鲸吞之计,作孽更大矣。仰即遵批更正,毋稍固执。切切。此缴。
(载于〈清〉樊增祥:《樊山政书》,那思陆、孙家红点校,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95-9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