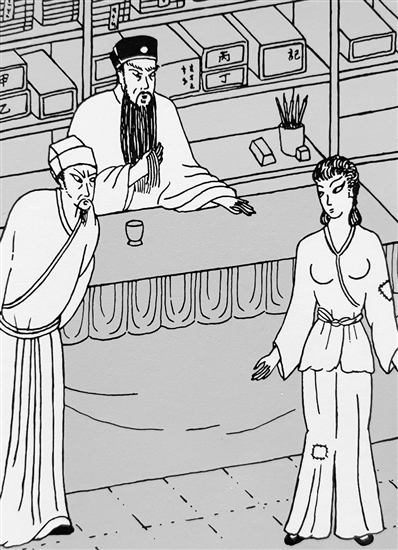 决狱图,高罗佩绘,选自Der Affe und der Tiger
决狱图,高罗佩绘,选自Der Affe und der Tiger
《清明集》里还有一位判词高手,唤作秋崖。秋崖是号,本姓方,名岳,字巨山,祁门人。却说这方岳,本色竟是一位诗人,有《秋崖小稿》行于世。钱锺书《宋诗选注》一口气选了他三首,并有这样的评价:
南宋后期,他的诗名很大,差不多比得上刘克庄。看来他本来从江西派入手,后来很受杨万里、范成大的影响。他有把典故成语组织为新巧对偶的习惯,例如元明以来戏曲和小说里常见的“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语人无二三”这一联,就是他的诗。
钱锺书说的那首诗叫作《别子才司令》,全文是这样的:“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语人无二三。自识荆门子才甫,梦驰铁马战城南。”写这首军旅诗时,方岳刚出道不久,担任兵部侍郎、淮东制置使兼知扬州赵葵的幕下干官。端平二年,窝阔台率蒙古大军南侵,两淮边防亦紧,高邮就暴发了军哄事件,方岳受命平定其变,“戮首恶数人,一城帖然”。赵葵曰:“儒者知兵,吾巨山也。”
不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另一首《甘蔗》,其诗云:“老境于我渐不佳,一生拗性旧秋崖。笑人煮箦何时熟,生啖青青竹一排。”“一生拗性”,真是活脱脱地画出了他的性格。有意思的是,方岳的“拗性”,还专爱冲着当朝丞相去撒。第一个撞上枪口的是史弥远。据洪焱祖《方吏部岳传》讲,“岳七岁能赋诗”,长入郡庠,“文章气概名天下”,不意在科举考试中因为语侵史弥远,吃了大亏。方回在《跋方秋崖壬戌书》中讲:“邵定壬辰,秋崖别省第一人,殿试本亦第一,以语侵弥远,为甲第第七人。”
史弥远之后是史嵩之。《方吏部岳传》云:“先是,史嵩之在鄂渚,王楫划江协和,嵩之主和议。秋崖代葵稿书,责嵩之,以此取怒。”后来嵩之入相,方岳乃遭挟嫌报复,致使在家闲居四年之久。四十九岁时,好不容易才东山再起,除知南康军,但他仍旧脾性不改,又在此任上与另一权相、时任京湖制置使兼湖广总领的贾似道大干一场。《方吏部岳传》记此事甚详:
知南康军,郡当杨澜左蠡之冲,风涛险恶,置闸以便泊舟。湖广总领所纲梢,据闸口,邀民钱万,始得入闸。民船有覆溺者。取纲梢榜之百。京湖阃兼总领贾似道怒,谓无体统,移文令岳具析。岳怒谓:湖广总领所,岂可于江东郡寻体统?大书判数百语,有曰:“岂不知天地间有一方岳。”
乾隆时人陈淼说:“观其复贾似道书,有曰‘岂不知天地间有一方岳’,斯言非惟使当日权奸丧魄,虽千载而下,读之犹觉凛凛然有生气。”方岳复贾似道书的全文,周密的《齐东野语》中有记载,读来真是荡气回肠。
总领虽大,湖广之尊;南康虽微,江东列郡。当职奉天子命,来牧是邦,初非总领之幕客,亦非湖广之属郡。军无纪律,骚动吾民;国有常刑,合从断遣,此首臣职也,于都吏何与焉?
据说,“贾公得牒,不胜其愤,遂申朝廷,乞行按劾。于是朝廷俾岳易邵武以避之。去郡日,有士人作大旗,书一诗以送之,曰:‘秋崖秋壑两般秋,湖广江东事不侔。直到南康论体统,江西自隔两三州。’”
所谓“秋崖秋壑两般秋”,秋崖自不待说,秋壑则是贾似道的号。“两般秋”,一秋是君子,一秋是小人,但君子与小人斗,败下阵来的总是君子。所谓“直道难行而诡遇易售,正不足以胜邪,大抵然也”。但方岳所要面对的小人,后面还有,也是一位国相,蓝面奸臣丁大全是也。那是在宝祐四年,得右相程元凤举荐,方岳出知袁州,不久,丁大全为右相兼枢密使,“以书属事”,令方岳为他“差船”“买钉”,以造私宅,方岳“不从”。丁大全乃嗾使江州制置副使袁玠劾罢方岳官职,甚至夺其考功印历,逼其“售田业偿之”。方岳于印历之上忿然题诗:“一钱太守今贪吏,五柳先生歙富民。”自此再无出仕之意,年六十四卒于故里荷嘉坞。
许多年后,清代一位叫李汛的,还在为秋崖的“禾生于莠”不胜唏嘘:
呜呼!先生之道虽晦于当时,先生之文则显于今日,不亦慰哉!虽然,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观其不与相使之求,廉也;不应客将之请,重也;不入淮阃之幕,介也;不准荆闸具析而还其文,刚也;馂(军)舟横境而榜之百,严也;廷对不讳,鲠也。特此屡挫而气不挠,虽困而节不移,屹然壁立,不可以犯,非自孟氏泰山岩岩中来邪!此尤为后人者之所当法。
这样一种刚介执拗、不畏强权的性格,天生就是做法官的材料。方岳仕途虽然短暂,但在历任南康、邵武、袁州太守期间,充分展现了他理讼治狱的非凡才能。《名公书判清明集》选录他的判词不算最多,但质量很高,独具特色。有意思的是,这些判词一反他“拗性”的本色,处处可见力透纸背的宽恕与仁厚。方岳亦是理学家,私淑朱子之学。巧合的是,他作为地方主官的第一个治所南康军,亦曾是朱熹做太守的地方。更巧的是,他们俩都是四十九岁那年入境南康。像他的前任一样,他也倡导仁政,关心民瘼,“圣朝本仁厚,鼠辈亦吾儿”,“天与君王共一仁,只将仁与物为春”,是他的治世理想。移风易俗,教化为先,这在他的判词中历历可观。例如在袁州任上,他有一道“惩教讼”判,立誓“为尔袁一洗之”,追回韩愈任太守时的淳厚风俗:
袁自韩文公时,称为民安吏循,守理者多,则其风俗淳厚,盖已久矣。不知何时有此一等教讼之辈,不事生业,专为嚣嚣,遂使脑后插笔之谣,例受其谤。为长吏者,要当为尔袁一洗之。太守入境之初,犹未交印,纷然遮道,谕遣复前,已厌其为喜讼矣。有一髽者,试呼而问之:“年几何?”曰:“十二。”“能书乎?”曰:“不能。”“则状谁所书也?”曰:“易百四郎。”心已知其为教讼之人,不可不追。问所以,则又有甚焉。盖易从书铺也,岂不知年尚幼,法不当为状首,而教之讼,其罪一。陈念三,后夫也,法不当干预前夫物业,而教之讼,其罪二。新知县方到,未给朱记,法不当为人写状,而教之讼,其罪三。初开杖封,政当断以奸猾,以厚风俗。从轻杖一百,枷项本州,其四县各令众五日,镂榜晓谕。后有教讼,非杖一百所能断也。勉自改业,毋犯有司。
又有一道“禁赌博有理”的榜文,也是从整治民俗出发:
四民之所不收,百害之所必至,始而赌博,终而盗贼;始而嬉戏,终而斗殴;始而和同,终而必争。败事丧家皆由此始,固官司之所必禁也。然禁戢者有司之责,信必者当职之令,有敢狃于习俗,视为故常,官有明条,决脊无容恕。备榜晓谕:输钱人自首,特原其本罪,追还其钱,却将赢钱人依条断令。
在这道榜文中,一方面明确宣布对于赌博恶习“官有明条,决脊无容恕”,另一方面,又给足从宽政策,申明如果“输钱人自首”,不仅可以“原其本罪”,政府还帮其“追还其钱”,只是“将赢钱人依条断令。”
在具体个案中,“亦可谓极其宽恕矣”的例子亦比比皆是。例如“进纳补官有犯以凡人论”判:
既是曾仕宦,必知上下之分、宾主之礼、朝廷之法也。一监税见州郡,礼固有数,乃敢大庭广众极口肆骂。入公门鞠躬如也,固如是乎?刘监税虽小官,然而袁州见任也,奉命守职,开锁放船,而乃两人露巾扭拽,以至州衙,殊骇闻听。据诸仆所供,乃知是妄。一进纳、七色补官,有犯以凡人论,而敢猖狂至于此乎!且其自书曰承信郎,而诸仆以为进武校尉,则是诈称官呼矣。张指使观其酒如已醒,请来问。
一个通过缴纳钱粮买取官爵的小吏,不仅撕扯履行职务的官员的官服,甚至大闹郡府,经讯问他的仆人,还存在“诈称官呼”的问题。方岳虽然觉着“殊骇闻听”,但却没有急着发威,因见其是酒后生事,便吩咐张指使待他酒醒后再加审问。案子查清楚了,结果却是放人,背后究竟是如何考量的?方岳在“免缴出身文字断仆讫申曹司并申部照会”判中写得非常清楚:
鬻爵多财,士类所不齿。然既已从仕,便当循规守矩,顾乃猖狂妄行,自同小辈。当职虽不肖,然袁州朝廷之一部,入公门如不容,而大声疾呼,略无忌惮,是无州郡也。刘监税奉州郡之命,点放船只,有司之守也。何物小吏,敢毁其冠、裂其衣,通都大衢,观瞻甚骇,是无有司也。朝廷爵级,所以励世磨钝,岂容妄自增加。校尉也而辄称承信,是无朝廷也。无州郡可也,无有司可乎?无有司可也,无朝廷可乎?本合缴出身文字,申朝廷、取指挥,又念千钧之弩,不为鼷鼠发机。案以绫纸责还,令其逐项交领。其点到客货客船亦一并还之,并取领附案,两仆佥厅决二十,放。当职所以待之,亦可谓极其宽恕矣,然观此辈,必一小人,道遇洪都,安知其不妄有陈溷。备具本末申漕司,并申部照会。
方岳手下留情的主要考虑是:“本合缴出身文字,申朝廷、取指挥,又念千钧之弩,不为鼷鼠发机。”通俗一些讲,就是“杀鸡焉得用牛刀”。酒后失态,大闹府衙,说大也大,说不大也不大。方岳的判词,规矩讲得不能再明白了,他觉得这也就够了,法律之弩,还是留待射向那些更值得一射的豪横奸徒罢。
得饶人处且饶人,不是遑顾是非,不是放弃原则,不是恂私枉法,而是有着更为宽广的仁厚之念。来看一道“诉族人行盗”判:
骆伯友诉所失,不过锡瓶、布袋耳,而搜之族,则功缌之亲也。昔人有遭盗者,曰:“幸深夜无人知,吾若执尔,遂使尔终身受盗贼之名,吾不忍也。”彼于凡人尚能如此,而况同曾大父之叔姪乎!遂使干连者数人,缭绳者数月,学者不如此也。学司除学籍,余人放。
“吾若执尔,遂使尔终身受盗贼之名,吾不忍也。”古人的这一理念颇为发人深思。盖刑罚之具,在于惩恶扬善,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但若“锡瓶、布袋”者流,动辄送狱,狱满为患不说,那人也一日为贼,终身为贼,遂为社会之对立面矣。尤为恐怖之处在于,其背后例有受其牵连之亲故,则负面情绪难保不会以几何级数无限放大。此维稳乎?此为不稳乎?
方岳之为方岳,决非一意从宽,而是当宽者必宽,不当宽者毫不含糊。而在这宽与不宽之间,则透出厚人伦、美教化的鲜明导向,成风化人,润物无声。这方面的经典之作,当推“祖母生不养死不葬反诬族人”判:
阿王生而孤老,所当供养者其子孙也;死而葬埋,所当经理者其子孙也。子孙零落,独有一胡师琇尚存,乃飘弃出家不顾。祖母生则族人养之,死则族人葬之,为师琇者,尚何面目立天地之间哉!族人裒金而葬,以其不利也而迁焉,与其他发掘塚墓不可同年而同语也。使当职处此,迁葬者本自无罪可科。今所司既为将两人勘锢,监迁原处,为师琇者亦可已矣,至经上台,嚣讼不休。然则养其祖母,葬其祖母者,乃师琇之仇人邪?不可谓知恩报恩者矣!此盖贩卖丘中之骨未满其意。亲死之谓何?又因以为货,不孝者也。在法:“供养有缺者,徒二年。”此师琇祖母在时之刑也。“骨肉相弃,死亡不躬亲葬敛者,于徒二年上重行决配。”此师琇祖母死时之刑也。罪在“十恶”之地,从轻杖一百,编管邻州,申,照会。
生不养死不葬,律有明条,罪有应得。被诬的族人,正是生则养其祖母,死则葬其祖母之辈,“自无罪可科”。本案的难点,在于做善事的族人因为觉得不吉利,又将其祖母的坟墓迁葬。胡师琇正是抓住这点,以“发掘”坟墓之罪将其诉至官府。祖墓神圣,不可侵犯,法之所禁,自古而然。《清明集》中,亦不乏此类讼争。蔡久轩“一视同仁”判就云:“岂特姨奶坟不可动,虽古墓亦不可动也。国家法律,一视同仁,岂有所轻重哉!”族人毕竟动了人家的祖墓,具备“发掘”坟墓的行为要件,换作一般官吏,当会依律定罪,但方岳却作出截然相反的裁决,认为“与其他发掘塚墓不可同年而同语也”。他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不是只盯着法律的具体条款,而是本其事,原其志,轻重相举,以德坊民。
古人讲:“法有正条,理宜科结。”但法律绝不仅仅只是指某个具体条款,法律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看似依法,很可能恰与法律的精神背道而驰。方岳无疑具备很强的体系思维,这也是他能够“不畏浮云遮望眼”,法理事理情理理理相通的重要基础。我们此前说到过的“契约不明,钱主或业主亡者不应受理”判,就是一个突出例证:
读刑臺台判,洞烛物情,亦既以郏氏为不直矣。然郏氏非,则汤氏是,二者必居一,于此而两不然之,举而归之学官,此汤执中之所以不已于讼也。披阅两契,则字迹不同,四至不同,诸人押字又不同,真有如刑臺之所疑者,谓之契约不明可也。在法:契要不明,过二十年,钱主或业主亡者,不得受理。此盖两条也。谓如过二十年不得受理,以其久而无词也,此一条也。而世人引法,并二者以为一,失法意矣!今此之讼,虽未及二十年,而李孟传者久已死,则契之真伪,谁实证之,是不应受理也。合照不应受理之条,抹契附案,给据送学管业。申部照会。
能将“法意”融会贯通,此其一也;能够将“法意”准确完美地表达出来,此又一也,二者缺一不可。方岳族裔方谦尝云:“文岂易言哉,亦岂易传哉!”方岳的诗词文章能够代代相传,除了其性格为人之“雄才奇气”,文字本身之“以意为之,语或天出”,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秋崖之好,好就好在不仅诗好,词也好,判词更好。这道“寺僧争田之妄”判,就具有“天出”之美,那一连十“妄”,既营造出一股排山倒海之势,又有如一根丝线,将纷纷然诸般情状,串联得井然有序:
妙缘院可谓无理而嚚讼者矣。执出砧基,独无结尾一板,安知非经界以前之废文,去其岁月,以罔官府之听乎?其妄一也。以此难之,则曰绍兴十九年,江西经界已成,此其年之砧基也。既无岁月,何凭为绍兴十九年之砧基乎?其妄二也。假如其说真为经界文书,而吴承节公据,又在绍兴三十年,如此则前十年之文书,久已为废纸矣,其妄三也。吴承节公据,乃官司备坐勑旨,将没官户绝田出卖,明言:“承买妙缘院违法田产”,时则此田,乃没官之田,非常住之业,其妄四也。出卖没官之田,乃是绍兴二十八年指挥后之公据,请买之时,岁月正合,而谓之强占,其妄五也。吴氏纳钱于官,初非买田于寺,而谓寺院香火不绝,断无卖之理,其妄六也。自绍兴三十年,至淳祐十二年,凡九十三年为吴氏之业,而一日兴词,其妄七也。合而言之,次田乃妙缘院违法没官之田,官司之所召卖者,于寺僧何与焉?违法于百年之前,嚚讼于百年之后,其妄八也。批阅案卷,凡经五断,而章司户所拟,特为明允。寺僧敢污以货,谓之恕断,其妄九也。以“交易法”比类言之,“契要不明,而钱业主死者,不在受理。”今经百年,吴氏为业者几世,寺僧无词者几传,而乃出此讼,其妄十也。僧中罗刹,非斯人也而谁?本合重科,以赦漏网。吴承节执据管业,妙缘砧基批凿给付,如敢顽讼,则讼在赦后,幸不可再矣!门示。
明朝的时候,盛时选将出按辽左,临行前见到张四维自《永乐大典》撮录之《名公书判清明集》,取而阅之,谓“读律者必知此,庶几谳拟不谬”,遂携入辽。谳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撰写裁判文书。又是许多年过去了,当我们今天知道了方岳以及方岳同僚们的这些判词,庶几也会有所收获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