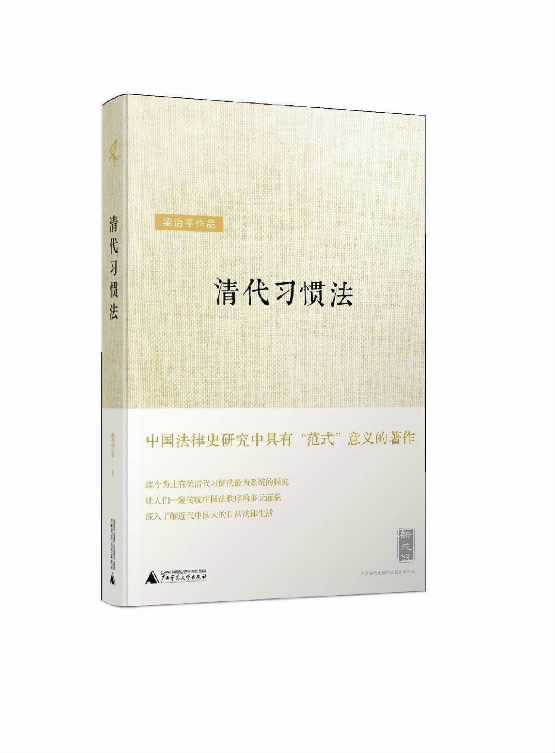
梁治平先生的《清代习惯法》被冠以中国法律史研究中具有“范式”意义的著作,笔者认为是名副其实,并不过誉。对于法律史的研究,在我国也是一个较为热门的学术领域,其为推动今天的国家法治建设,增进社会公众的法治思维观念,滋育和丰富司法机关文化软硬件建设等方面都具有积极价值和深远意义。法律史研究虽多发端于理论层面的探掘、剖析,但对于当下的法治建设仍然大有裨益。
关于近代法律史,在打破两千多年封建传统观念禁锢的同时,也在承袭诸多传统文化精粹和悄然汲取域外有益法律理念,更加充实了中国法秩序的多元架构。相较于时下我国法学界一些厚重饱满的巨作,治平先生的这部著作算不得“大部头”般的学术成果,但从其研究内容而言,却可谓“集约、系统、精深”。
治平先生在该书的“导言”部分表明了该部著作的研究侧重点即是“从大传统转向小传统,从官府的法律转向民间的法律,或者,更确切地说,从国家法转向习惯法”。他的着墨重心就是在“习惯法”。中国社会自古以来运用法律实施治理的传统相当久远,秦汉以来的历朝历代即有大量法律典章沿袭流传。对应中国古代社会的结构和形态,治平先生关于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有着理性清醒的认知,二者关系是一种相互渗透、配合,又彼此抵触、冲突的呈现,结果就是界限变得愈发难以辨识。他的视野并没有局限于此种内在传统关系往复交合下的本土观念,而是乐于导入外域思维对研究内容加以拓展论证,比如他所关注的马克斯·韦伯、罗伯托·昂格尔、韩格理等西方学者从社会学、经济学等层面对于习惯法的分析和探究,因其试图把中国法律史的材料纳入一种社会理论框架下的宏阔视角思考,赋予了法律史更为深厚广博的底蕴,也让我们的思域触角得以延伸。
《清代习惯法》在引经据典之余,更建立在对一些地区遗存的明清契约文书的探寻研究基础上,以佐证清代习惯法的发展历程。治平先生的笔触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对清代习惯法进行深入考察,一系列繁杂的清代司法档案明示,让习惯法在形式上表现为“乡例”“俗例”“乡规”“土例”等,习惯法既非人定,其规范自然缺乏如成文法一般固定的形式,乃至因地而异,随时而变,但又不意味着习惯法上的规范无从寻觅,更不意味着我们应当放弃寻找和描述这些规范的努力。正确的做法应当是由习惯法所固有的形态入手去发现和阐明其规范。无疑,他是理性和明智的。较之西方法律世界所谓的“法谚法语”,治平先生结合其发现的我国能够“构成习惯法基础的最坚固最基本的材料”,对民间流行的各种习惯语作以深度辨析,让我们知晓大量的“法语”产生于乡民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生活、劳作和交往中,它们以浓缩的形式一方面表达了习惯法上各种相对固定化了的关系,一方面给予这种关系以更加确定的内涵。被视为习惯法上的“规范”的“法谚”,在表达原则的同时,更直接规定了有关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这些民间习惯语乃是习惯法最有力最明晰的表达,因其存在形式本身,适足表明习惯法的性质和特征。
在研究习惯法的起源时,治平先生指出习惯法因其出于自然,其包含两重含义,其一为习惯法并非出于立法者的意志与理性,而是由民间日常生活中自动显现。其二为习惯法由“自然”塑造而成,此所谓自然,既指实际的生活秩序,也包括山川风物、民俗人情。今天想必无人否认历史条件、地理环境乃至于人口数量、气候变化等等都会对习惯法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这就是一种“自然”和“应然”,世间万物的辩证规律尽在其中,这就是他所说的“习惯法不仅出于社会常态,也可能由社会变动造成”。“自然”势必难以脱离人的情感、思虑、理性、欲望,一定程度上也拉升到了一个哲学的层面,史实的盘点间、文字的跃动里,治平先生也贯穿以对法哲学的思辨,在努力考略、揭示习惯法制度内在关联的同时,不会让一些论点流于形式浮于表面,其间迸发出的智慧光芒照亮读者思域暗角之余,又启人沉思,促人省思。
关于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分野,在明示二者系不同知识传统,分别受不同原则支配,归结出其久已形成“分工”格局,但二者仍不乏相互的“配合”,在长期演进和互动过程中形成彼此渗透之势,引用清代名幕汪辉祖所认为“官之所难为者,莫患于上下睽隔”。故其建议新官初到务要“体问风俗”,如此理事方可“情法兼到”。其中已如治平先生所言“国家法与习惯法之间的关系就现出某种简单的逻辑”,先不必细究数百年前的司法,沿袭于今,何尝不就是在“情理法交融”中折射体现法的价值本位?一以贯之的法文化传统在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本就是有着或隐或现的共通之处,治平先生也是通过对清代习惯法的勤苦耙梳,让我们建立在丰盈法学研思基底之上,更加确信和致力于践行传统法秩序和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礼法”轨仪,令学术和实务的距离愈发亲近。
(作者单位: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





